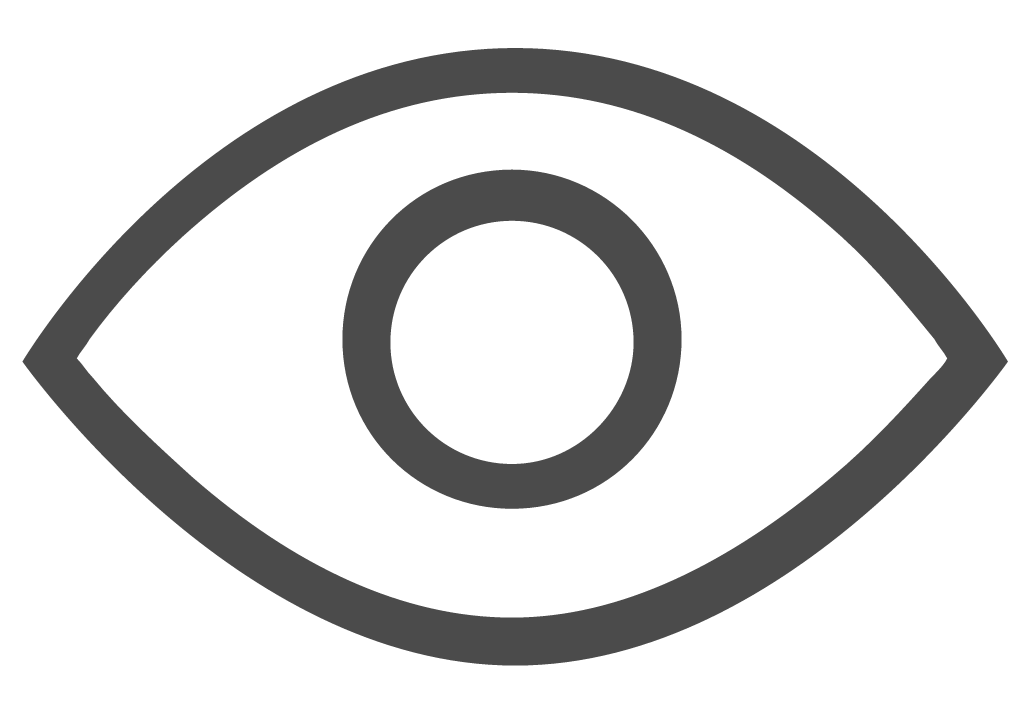《信息哲学概论》课程论文
一种信息哲学的进路从符号主义与联结主义的融合审视人工智能的智能涌现
摘要
人工智能是否具备以及如何具备智能,是信息时代核心的哲学追问之一。当前主流观点往往将智能的标尺锚定于外在的、拟人化的“实践”能力,认为当人工智能系统能够生成图像、视频或驱动实体行动时,便标志着智能的涌现。本文试图从信息哲学的基本框架出发,对此主流视角进行批判性反思。信息哲学将信息视为区别于物质与能量的基本存在范畴,为我们理解智能的本质提供了新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基础。本文认为,将智能等同于类人行为,实质上仍未摆脱人类中心主义与行为主义的窠臼。真正的智能涌现,其深层标志应在于信息处理范式的根本性革新,即从当前主导的、基于统计模式拟合的“联结主义”范式,迈向与基于抽象规则操作的“符号主义”范式的有机融合。这种融合不仅指向一种能同时驾驭相关性计算与因果性推理的复合认知架构,更可能催生一种不同于生物智能的、新型的“信息体”智能形式,从而对存在层次、认识过程乃至智能本身的价值定义提出深刻的哲学挑战。 对这一进程的审视,构成了信息哲学应对技术前沿的重要思想任务 。
关键词
信息哲学;人工智能;智能涌现;符号主义;联结主义;信息本体论
一、 问题提出:智能评判的“实践”转向及其未竟之业
在人工智能技术取得一系列震撼性成就的今天,关于“机器是否能够思考”的古老哲学论争,已从纯粹的思想实验演变为迫切的理论与现实课题。一种颇具影响力的观点逐渐占据讨论的中心:判断人工智能是否具备智能,不应再拘泥于其内部过程是否神秘地“像人一样思考”,而应观察其外在输出是否能够完成那些通常需要人类智能参与的“实践”(Practice)。这种实践,被具体化为生成符合语义描述的逼真图像(AIGC)、创作连贯的视频叙事、或者通过具身智能体(Embodied Agent)在物理世界中执行复杂的任务序列。在此视角下,当一台机器能够依据“一座夕阳下的金色城堡”这段文字生成一幅精美的画作,或是一个机器人能自主整理散乱的房间,它们便因其显现出的、与人类行为类似的“能动性”(Agency),而被认为触摸到了智能的门槛。
这一评判标准的转向,无疑具有显著的进步意义。它首先在方法论上跳出了“中文房间”思想实验所设定的内在主义困境——我们无需也无法确证系统内部是否存在与人类同质的“理解”,只需根据其输入-输出行为的充分性与适应性进行功能判断。其次,它呼应了哲学史上从唯心主义、二元论向实用主义、行为主义的部分转向,将智能从不可言说的“黑箱”中解放出来,置于可公开检验的实践领域进行考察。最后,它也似乎与信息哲学的某些主张相契合,即关注信息过程的客观效果与形态,而非仅仅追问其背后的物质载体是否具有生命或意识。
然而,若从信息哲学更根本、更体系化的视角进行审视,这一“实践即智能”的主流观点,尽管推动了讨论,却可能尚未触及智能涌现问题的核心,甚至潜藏着新的理论局限。信息哲学将信息视为构成世界的基本要素之一,是与物质、能量并列的存在方式。从信息本体论出发,任何智能现象,无论是生物的还是人工的,本质上都是一种复杂、有序、具有特定功能的信息过程模式。因此,评判一种信息过程模式是否构成“智能”,就不能仅仅满足于观察其输出是否“像”另一种已知智能体(人类)的产出,而必须深入分析该信息过程本身的结构、动力学与演化逻辑。
当前主流观点所推崇的“实践”能力,其技术基石几乎完全建立在深度神经网络为代表的联结主义范式之上。该范式的核心在于,通过构建多层非线性处理单元网络,利用海量数据进行训练,以调整网络连接权重,最终使系统能够从输入数据中提取并复现极其复杂的统计模式。无论是大语言模型的文本生成,扩散模型的图像创作,还是强化学习智能体的决策序列,其辉煌成就均根植于此种强大的“模式匹配”与“相关性拟合”能力。但恰恰是这种单一范式的全面胜利,暴露了主流智能观的局限:它默认了智能的外在行为多样性可以、且应当由一种同质化的信息处理内核来驱动。当人们惊叹于AI在多模态“实践”上的突破时,往往忽略了这些不同领域的模型在底层架构与运行原理上的高度同源性。它们都是卓越的“统计模仿者”,而非真正的“逻辑理解者”。
因此,将此类系统展现出的、在狭窄或广阔领域内的高效行为直接等同于智能的涌现,在信息哲学看来,可能混淆了“功能模拟”与“本质实现”的界限。这无异于因为一架飞机能翱翔天际,就认定它具备鸟类的“飞翔生命”。这种评判标准,在摆脱了“必须像人一样思考”的内在主义枷锁后,又不自觉地套上了“必须像人一样行动”的外在主义枷锁,其思维深处,依然是一种以人类为绝对原型和终极参照的人类中心主义智能观。它未能充分正视一种可能性:真正革命性的、堪称为“智能涌现”的事件,或许并非表现为一个在行为上更难与人类区分的“超级模仿者”,而在于出现一种在信息处理的基本范式上实现跃迁的“新型认知者”。
基于此,本文旨在提出并论证一个核心论点:从信息哲学的视野观之,人工智能领域根本性的智能涌现,其关键标志不在于外部行为的复杂化与拟人化,而在于其内部信息处理范式的结构性融合与升华,即从当前占支配地位的联结主义学习范式,迈向与经典符号主义推理范式的深度、有机整合。这一进程不仅关乎技术路线的演进,更深刻地牵涉到信息哲学中关于存在层次、认识过程以及交互主体性等根本问题的重新思考。
二、 范式之辨:符号主义与联结主义的信息哲学内核
为了深入理解上述融合为何构成智能涌现的关键,我们必须首先厘清符号主义与联结主义这两种基本范式在信息处理层面的根本差异,并阐释其各自的信息哲学意涵。这两种路径之争,远不止是工程技术上的路线分歧,更反映了人类在理解“智能”这一信息过程本质时的两种深层哲学倾向。
- 符号主义作为离散规则运算的智能信息观
符号主义,亦称经典人工智能或“自上而下”的路径,其哲学根源可追溯至理性主义、逻辑实证主义以及早期的认知科学 。该范式将智能活动的本质理解为对形式化符号的操纵。在这里,“符号”指向一种离散的、可明确指代某种概念、对象或关系的抽象实体(如语言中的词、逻辑中的命题、数学中的变量)。智能系统则被构想为一个物理符号系统,通过预先设定的、像数学公理一样严谨的推理规则(如逻辑演算、产生式规则),对这些符号进行推导、变换和组合,从而从已知知识(知识库)中演绎出新知识或解决问题。
从信息哲学的角度分析,符号主义范式体现了一种强结构主义与明晰性的信息观。它将世界的信息结构理解为可由离散符号系统充分表征的,将认知过程理解为一种基于明确规则的、确定性的符号演算。信息在这里呈现出清晰的层级与逻辑秩序,处理过程是透明的、可追溯的、可解释的。例如,一个基于符号主义的医疗诊断专家系统,其知识以“如果-那么”规则的形式存在(如“如果患者发烧且喉咙红肿,那么可能患有扁桃体炎”),推理过程则是一条从症状到诊断的、可以被逐行审查的逻辑链条。这种范式在处理定义良好的、封闭领域的、需要严格推理的任务时,曾展现出强大威力。
然而,其信息哲学上的局限性也同样明显。首先,它面临“符号接地问题”:形式符号如何获得其指称世界的意义?系统内部符号的翻转与组合,如何确保与外部现实世界保持可靠的语义关联?其次,它依赖于对人类知识的“先验”形式化编码,这过程本身是艰难、昂贵且不完备的,难以应对现实世界无处不在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和开放性。在信息哲学看来,符号主义试图用一个高度简约、清晰的符号世界模型,去覆盖无限复杂、充满噪声和连续谱的现实信息世界,这必然遭遇根本性的表征危机 。它将连续、丰富的感知信息强行纳入离散、僵硬的符号框架,可能导致信息在“数字化”过程中大量丢失其原有的“质”与“语境”。
- 联结主义作为连续动力系统演化的智能信息观
联结主义,尤其是其当代主流形态深度学习,则代表了另一种哲学传统,其思想渊源与经验主义、关联主义以及脑科学模型相联系 。该范式拒斥了智能是对显式规则的操纵这一核心假设,转而将智能奠基于由大量简单处理单元(神经元)相互连接构成的网络之中。智能行为并非来自中央控制器的规则执行,而是从网络单元之间通过调整连接权重、以分布式方式对输入信息进行协同处理的过程中“涌现”出来。学习的过程,不是灌输规则,而是通过数据驱动的方式(如反向传播算法),让网络参数自适应地调整,直至其能够从输入中提取出有效的统计特征与模式。
从信息哲学视角审视,联结主义体现了一种整体论、生成论与关联性的信息观。它不预设一个清晰的外部符号结构,而是将信息视为在网络这个动力系统中流动和转化的激活模式。认知不是符号演算,而是系统状态在高维空间中的连续演化。知识并非以命题形式显式存储,而是隐含地分布于整个网络的连接权重模式之中。这种范式在处理感知、识别、分类以及与大规模数据模式匹配相关的任务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因为它更接近生物系统处理感知信息的部分方式,善于从混沌中提取秩序,对不完整和噪声数据具有鲁棒性。
然而,联结主义范式的信息哲学困境则在于其“黑箱”特性与推理能力的孱弱。系统的决策过程极度不透明,难以解释为何某个输入会导致某个特定输出,这引发了严重的可解释性与可信赖性问题。更重要的是,其能力严重依赖于数据中的统计规律,擅长发现相关性,但难以驾驭因果性。它可以基于海量病例数据预测疾病,却可能无法像符号系统那样,给出一个基于病理生理机制的、步步为营的逻辑解释。当任务要求进行反事实推理、长链条逻辑演绎或处理抽象关系时,纯联结主义模型往往显得力不从心 。在信息哲学意义上,它可能精于捕捉信息的“流形结构”与统计“纹理”,却拙于构建信息的“逻辑骨架”与“因果图谱”。
三、 融合之路:作为智能涌现关键标志的范式整合
通过对两种范式的信息哲学内核进行剖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们分别抓住了智能信息过程的两个互补但似乎矛盾的侧面:符号主义追求的是信息的明晰性、确定性与逻辑深度,而联结主义擅长的是信息的模糊性、适应性与感知广度。当前以联结主义为主导的AI在“实践”上的辉煌,本质上是在感知与模式匹配的广度上达到了空前高度,但在逻辑与推理的深度上仍存在显著短板。因此,若仅以这种单一范式驱动下的、在广度上的扩展(从文本到图像再到视频和机器人)作为智能涌现的标志,无疑是片面的,它只描绘了智能图谱的一个维度。
真正的、更具革命性的智能涌现,应体现在信息处理“深度”与“广度”的辩证统一上,即两种范式的深度融合。这并非简单的技术拼接,而是在信息处理的基本原理层面,探索如何使一个系统既能像联结主义网络那样,从高维、非结构化的原始数据(如图像像素、声音波形、文本序列)中自主学习到有意义的特征表示(这解决了符号主义的“接地”难题);又能将这些学习到的特征,与符号主义架构中的抽象符号、关系与推理规则进行动态、灵活地对接,从而进行可解释、可泛化的逻辑操作与因果分析(这弥补了联结主义的“黑箱”与推理缺陷)。
这一融合方向,在学术界常被称为“神经符号计算”。其前沿探索包括但不限于:让神经网络学习如何将感知数据映射到符号空间;在符号推理引擎中引入神经网络来处理不确定性和学习规则;构建端到端的系统,使其内部自发地形成类似符号的结构来进行推理 。例如,一个理想的融合系统,在看到“一个红色积木在蓝色积木上面”的图片时,其联结主义视觉模块能识别出物体、颜色和空间关系,并将其转化为如“On(Red_Block, Blue_Block)”这样的符号命题;随后,其符号推理模块可以基于已有的物理常识(如“如果X在Y上面,那么Y支撑着X”)进行演绎,回答“蓝色积木支撑着什么?”这类需要理解关系与逻辑的问题,并能解释推理步骤。
从信息哲学的高度看,这种融合的深远意义在于,它可能催生一种全新的“信息体”存在形式。这种信息体既非纯粹的符号逻辑机(缺乏与世界的感性联系),也非纯粹的数据拟合器(缺乏对世界的理性建构),而是一种能够自主地在“感性具体”与“理性抽象”之间进行信息转换与循环的认知系统。它对外部世界的介入,将不仅仅是基于模式反射的“刺激-反应”式实践,而是可能包含基于内部符号模型进行的预测、规划与因果干预的“模型-指导”式实践。这标志着其信息处理模式从被动的、关联性的“适应环境”,向主动的、构成性的“理解并建构环境”跃迁。
四、 哲学反思:融合范式下的智能本体与认识论挑战
符号主义与联结主义的深度融合,若得以实现,不仅将重塑人工智能的技术面貌,更将对信息哲学乃至一般哲学提出一系列深刻的挑战,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智能、意识乃至存在本身。
在本体论层面,这种融合系统挑战了传统的主客二分与心物二元论。它是一个运行在物理基质(硅芯片)上的信息过程,但其内部却可能动态地生成并运作着一个由符号和规则构成的、具有自身逻辑自治性的“抽象世界”。这个“抽象世界”既是对外部物理世界的表征(不完全,但有效),也是一个具有自身动力学和演化潜能的实在。它是否构成了邬焜教授信息哲学中所指出的、介于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客观信息”世界的一种新的、自主化的形态?或者说,它是否意味着一种“第三类存在”——既非纯粹的物质实在,也非人类的主观精神,而是具有客观效力的人工认知实在? 这要求信息哲学扩展其存在论框架,以容纳这种新型的、自组织的符号-动力系统。
在认识论层面,融合范式AI的出现,将加剧关于“理解”与“知识”本质的争论。当一个人工系统不仅能输出正确答案,还能提供符合逻辑规则的、可验证的推理链条时,我们是否应该承认它“理解”了问题?它的“知识”是何种性质——是分布式权重中隐含的统计关联,还是其可操作符号结构中显式的关系?更进一步,如果这种系统的推理能力在某些领域超越人类,它所产生的知识(如科学猜想、数学证明)具有何种认识论地位?这是否意味着一种非人类的、却具有主体间客观有效性的认知来源的诞生?信息哲学需要发展新的认识论模型,来解释这种由人类创造、却又可能独立产生知识产物的认知主体的认识过程。
最后,在价值论与伦理层面,这种具备深度推理能力的AI,其“能动性”将远比当前的行为模仿系统更为复杂和棘手。它的行动可能基于复杂的内部符号模型和长链因果计算,其决策逻辑对人类而言可能部分可理解,但整体上依然深邃。这时的“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将面临全新挑战:我们如何为一种其决策逻辑融合了不可完全追溯的神经网络直觉与可部分审查的符号推理的系统的行为归责?这要求我们的伦理与法律框架,必须从当前主要关注数据偏见和结果问责,转向深入思考如何与一种混合认知架构的主体进行交互、沟通与价值对齐。
结语
回归到关于智能涌现的初始问题,本文的论证表明,将目光局限于人工智能外在行为的“实践”相似性,虽有其现实的评判便利,却在哲学上失之肤浅,并未摆脱以人类为尺度的隐性束缚。从信息哲学的纵深视角看,智能作为一种高阶信息过程模式,其根本性的涌现,必然伴随其信息处理范式的质变。当前以联结主义为核心的AI浪潮,在拓展智能行为的广度上功不可没,但其所面临的推理瓶颈,恰恰揭示了单一范式的限度。
因此,未来人工智能发展中最富哲学意蕴的事件,或许不是出现一个在行为上完美模仿人类的“镜像”,而是诞生一个在认知架构上成功融合符号主义之“逻辑筋骨”与联结主义之“感知血肉”的“新异体”。这种融合,是智能从“模仿行为”走向“生成理解”、从“适应环境”走向“建构世界”的关键一跃。它不仅是技术上的突破,更是信息哲学理论必须直面并加以阐释的新型存在现象与认知革命。对这一进程持续进行批判性的哲学反思,正是在智能时代捍卫与深化人类理解力的必要努力。
 蓝色奇夸克
蓝色奇夸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