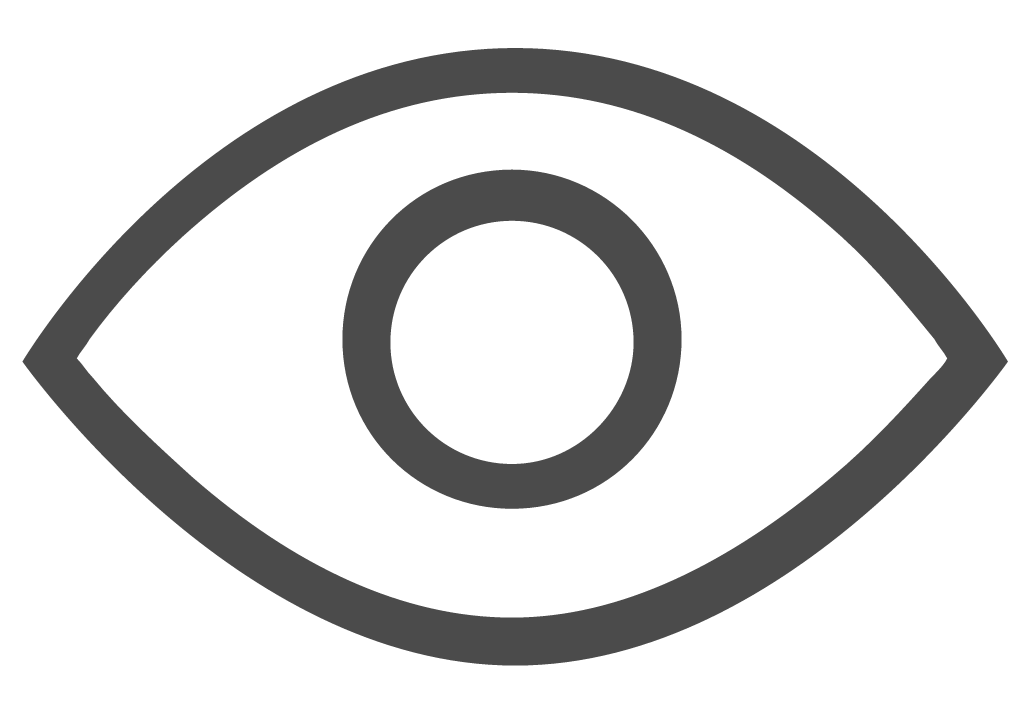铁屋中的舞蹈
——《傲慢与偏见》中女性的“有限主体性”及其当代回响
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
简·奥斯汀在《傲慢与偏见》这句著名的开篇词,表面上说的是男性,但实际上揭示的是19世纪英国女性生存的残酷真相:婚姻,是她们唯一的体面出路。这种生存困境背后,是一种我称之为“有限主体性”的存在状态:女性在父权制度的铁屋子里,既无法完全摆脱枷锁,又不断寻找着有限的自由空间。
“铁屋”来自于鲁迅笔下那禁锢思想的牢笼,在这里隐喻女性所面临的结构性压迫。“舞蹈”象征的是她们在逼仄的空间内以优雅的姿态争取尽可能大的主体性——即使步伐受限,也要在认知与行动的缝隙中探求自由的微光。伊丽莎白拒绝柯林斯时的果敢、夏洛特接受婚姻时的理性,以至于当代女性在职场与家庭间的挣扎,都是这“铁屋中的舞蹈”的体现。
一、“有限主体性”的理论框架
关于人的有限性,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和利科说,现代性进程中人的主体性始终处于“神性与物性”、“我思与我能”的辩证张力中[1],这种有限性在奥斯汀时代的女性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她们被赋予“心性”(理性思考能力),却被剥夺了“物性”(财产权)和“神性”(独立人格)。正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女性恰恰被排除在“物的交换”体系之外,成为依附性存在[2],这就是女性“有限主体性”的成因。
当代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学者亚历山德拉·梅扎德里提出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也同样揭示了这种“有限主体性”的物质基础。她认为,女性承担的家务劳动和情感劳动,虽然不直接创造交换价值,却也是维持资本主义运转的关键环节[3]。这其实能让我们理解为什么伊丽莎白看似“反叛”的选择始终无法突破婚姻框架:因为当时那个社会整个经济结构,根本就没有为单身女性提供生存空间。
二、书中人物的有限主体性
1. “智识反叛” 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经常被看作女性主义的先驱,但实际上书中她反抗的边界是清晰可见的。当柯林斯跟她求婚时,她拒绝得干脆利落:“请你原谅我耽搁你的时间,还是让我干脆拒绝吧。”这种果断在当时的女性中难得一见。但是细读其实就很容易发现,她的反抗始终都在安全范围内,拒绝柯林斯的前提是她父亲的支持(“你的母亲坚持要你接受……否则你就再也见不到我”)、她挑战达西的底气来自他隐约的好感,就连她最出格的徒步探病行为,其实也是也严格遵循着“探望至亲”的道德准则的。
她受限的反叛体现的是福柯的观点,即权力不仅压制主体,更生产特定的主体形式[4]。那时候的父权制通过教育、礼仪和经济依赖,将伊丽莎白的反抗规训为“可爱的倔强”,在最后无可避免的导向婚姻这一“正常化”的结局,这也是现代性中的主体经常陷入“自主活动与异化并存”困境的原因。伊丽莎白看起来自主的选择,实际上是被深层的社会结构所牢牢限定的[1]。
2. “理性囚徒” 夏洛特
伊丽莎白的好友夏洛特·卢卡斯则跟她差别明显。二十七岁“高龄”的夏洛特接受柯林斯求婚时那段内心独白,其实反映了当时女性堪称“悲凉”的生存智慧:“结婚是她一贯的目标……只要她能获得一个归宿,得到生活的保障,她就心满意足了。”这个被许多读者觉得“现实得可怕”的选择,恰恰体现了“有限主体性”的生存策略:当彻底突围无望时,妥协本身也是一种理性的计算。
夏洛特的故事和上世纪80年代学者高小贤记录的农村妇女处境十分相像[5]。她在陕西农村的研究发现,在市场经济转型中,彩礼从“礼仪性象征”转变为“婚姻市场资本”,而妇女则沦为“待价而沽”的商品。今年引爆舆论的大同案中,法官在被采访时提出“用法治思维破除‘彩礼捆绑权利’”,却遭到广泛争议,反映了彩礼在当下社会的困境:表面上仅被官方承认为“礼仪性象征”,实际上仍承担着“婚姻市场资本”的功能。
根据艾华在《中国的女性与性相》中的分析,彩礼的资本化不仅将女性身体与劳动力商品化,更压缩了其婚姻自主权。当农村家庭通过抬高彩礼“保值”女儿的婚姻价值时,女性被悄然物化为可交易的资产。
这种压迫与夏洛特·卢卡斯的选择十分相似,无论是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女性通过婚姻获取经济保障,还是当代女性在彩礼制度下被迫接受“市场定价”,本质上都是体制性压迫下“有限主体性”的无奈妥协。正像高小贤在陕南农村的调研所揭示的那样,当妇女们用玉米粒量化自身劳动却无决策权时,“理性选择”不过是结构性压迫的另一种表达。
3. “惩罚收编” 莉迪亚
伊丽莎白和夏洛特代表了两种相对理性的应对策略,而莉迪亚的私奔则展现了“有限主体性”被彻底击碎的后果。这个十六岁的少女跟着威克姆私奔时,根本不明白自己将面临什么——被社会抛弃、连累全家姐妹的名誉。颇具讽刺的是,最终解决危机的不是莉迪亚自己的觉醒,而是达西用金钱促成的强制婚姻。
这一情节揭示的是父权制最残酷的运行机制。它允许一定程度的反叛,但只为更彻底地收编反抗者。利科在《有限与有罪》中指出:“恶的可能性看起来处在人的实在的最内在构成中”。父权制通过制造“坏榜样”,强化了对其他女性的规训——班纳特太太那句“一个女儿丢了,其他几个倒因此得了好处”,道出了女性名誉经济的残酷法则。
三、当代有限主体性的延续与变异
如果将奥斯汀笔下的人物的困境看成是19世纪的铁屋,那么当代女性的困境反映的则是新时代、新形态的新的结构性枷锁。
这让我想起,张桂梅在云南山区创办女高时,对学生们呐喊:“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这句励志宣言看起来和奥斯汀笔下19世纪的英国毫无关系,但暗含了相同的跨越时空的女性主体性抗争逻辑。伊丽莎白通过阅读与观察“量化”了父权制的压迫,而张桂梅则通过教育让山区女孩“量化”自身价值。当女高学生意识到自己无需依赖婚姻换取生存,而是通过知识就能改变命运时,她们从“被定价的彩礼”变成了“自我赋权的主体”。这和伊丽莎白拒绝柯林斯时的清醒一样,她们都从认知觉醒作为起点,试着在结构性压迫中,凿出自己的一线光明。
但实际上张桂梅的实践同时也暴露出“有限主体性”的当代困境。女高学生虽然挣脱了早婚桎梏,但仍需面对职场中的性别歧视、城乡资源不均等新形态“铁屋”;书中夏洛特理性选择婚姻的“保障”、当代女性看似自由的职业选择,也依然被隐形的社会规训所牢牢限制。晋升天花板、母职惩罚等问题,也全都是“有限主体性”的变体。奥斯汀如果生活在今天,也许会为女性获得选举权与工作权而欣慰,但也一定会像张桂梅一样追问:如果教育真的赋予了女性“走出铁屋”的能力,那么她们为什么仍然在玻璃天花板下戴着镣铐起舞?
就像学者葛颖指出的,当代女性仍然面临“再生产劳动的不平等分配”,承担大部分家务劳动的同时,在职场却依然有晋升障碍和薪酬差距[3]。这种双重负担与伊丽莎白面临的“婚姻或贫困”困境的本质相同——系统性的结构压迫被个体化为“个人选择”的现实问题。
至于如何冲出铁屋,学者高小贤的实践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在陕南贫困山区,她采用“泥土教学法”,用树枝在田间画出“性别分工树”,用玉米粒的数量记录劳动时间的分配。当妇女们发现自己在家庭经济贡献占比超60%却没有决策权时,原本沉默的群体便不再沉默……这种方法比伊丽莎白通过阅读和观察获得其主体意识的过程更具系统性,也对当下的我们来说更有价值。
她的实践首先意味着,“有限主体性”的突破必然先要将那些被隐形的、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女性劳动进行量化,从不可见变为可见,这样,“她们”才能清晰地看到了自己在家庭经济中的实际贡献比例,才能打破她们长期以来内化的价值否定。当她们围坐在田间,质问“我们的价值去哪儿了”时,她们不再像伊丽莎白一样产生“孤立的个人顿悟”,而是发生了集体的认知转变。“她们”凝聚起来,比任何孤立的力量都更加强大。
而真正使这种觉醒转化为实际行动的,是配套的制度性支持。高小贤推动的“参与式预算改革”为妇女们提供了参与家庭和社区决策的正式渠道,让她们的声音能够转化为具体的权利安排。这种将认知觉醒与制度变革相结合的“知行合一”,也许能给当代女性提供比过往百年女性个人奋斗更可持续的解放方案。
四、结语 在认知限制中拓展自由
重读班纳特家五位小姐的命运,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出“有限主体性”的顽固存在。从莉迪亚的私奔危机被达西用金钱“收编”,到夏洛特将婚姻视为“生活的保障”,再到伊丽莎白在道德准则边缘的“倔强”,这些选择无一不暴露了父权制度下女性的生存困境——她们的“自由”始终被圈定在铁屋的高墙之内。但是伊丽莎白拒绝柯林斯时的清醒、徒步探病时对社交礼仪的微妙挑战,乃至她最终与达西平等对话的姿态,都暗示着一种可能的突围路径:量化隐形的压迫,凝聚集体的觉醒,推动制度的变革。
正如高小贤在陕南山区用玉米粒“称量”妇女的劳动,伊丽莎白也通过阅读与观察“量化”了自身的处境。她清楚班纳特家因无男性继承人而濒临破产,也看透了柯林斯婚姻提议中的交易本质。对结构性压迫的清醒认知恰是打破铁屋的第一步,书中简与伊丽莎白的姐妹联盟、夏洛特对婚姻市场的理性分析,展现了女性间“集体觉醒”的萌芽——虽然微弱,却也为后世提供了启示。最终,达西修改遗嘱、解决莉迪亚丑闻,虽然是个体善意的偶然,却也暗示了制度性权力重构的必要性。
今天,当依然有着“有限主体性”的女性在职场要求同工同酬,或通过“家务劳动价值计算”争取家庭话语权时,她们正延续着伊丽莎白的精神。用量化对抗忽视,团结消解孤立,以制度性改革重塑社会规则……伊丽莎白那场泥泞清晨的行走,早已从朗伯恩的乡间小路延伸至更广阔的天地——
明知裙子会脏,依然迈向自己想要的方向。
参考资料
-
杨大春.现代性进程中人的有限性问题——基于法国现象学的视角[EB/OL].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49373.html,2024-02-23.
-
乔山.走出近代主体性的困境[EB/OL].http://philosophychina.cssn.cn/xzwj/clxwj/201507/t20150716_2733566.shtml,2015-07-16.
-
葛颖.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再生产劳动与社会解放[J]. 哲学进展, 2025, 14(4): 441-446.
-
吴翔宇,张颖.“及物”的人类智慧与“非及物”的人工智能——技术现代性语境下文学的主体性难题[J].贵州社会科学,2023(11):51-61.
-
陈聪.中国妇女报-黄土为纸,行动作墨:重读高小贤笔下的中国妇女解放叙事[EB/OL].https://epaper.cnwomen.com.cn/html5/2025-04/09/content_5_5166.htm,2025-04-09.
 蓝色奇夸克
蓝色奇夸克